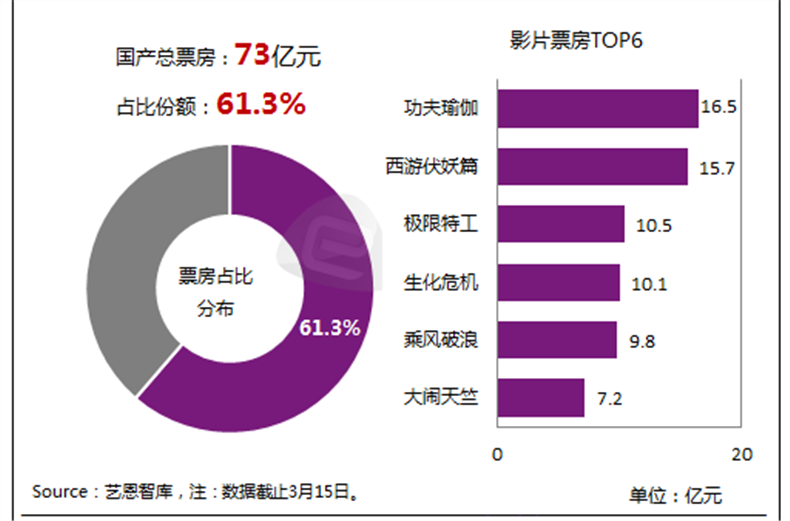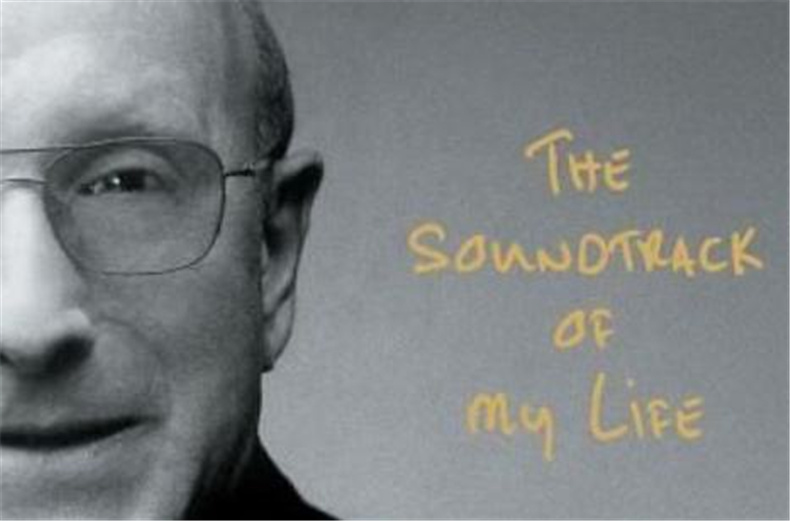拍出自己的长片处女作,是一个导演入行得到关注认可的第一步,比如昆丁花5万美元拍的处女作《落水狗》,南京的中国独立影像展在圣丹斯电影节首映后声名鹊起;克里斯托弗·诺兰拍于处女作1998年《追随》只花了6000美元,这部电影奠定了诺兰之后电影的风格。
但筹拍第一部长片同时也是最难的一步:写不好剧本,没有足够的钱开机、找不到合适的摄影师、美术指导、制片人,没钱请专业演员……
像王一淳就因为没钱做后期把拍完的电影《黑处有什么》放在家里的书架上,一放就是一年,“都长灰了”,这部电影花了300万,是她多年的积蓄,家人总打趣她:家里“放着一盘很贵的碟”。
幸好,所有的付出获得了回报,像本次我们专访的王一淳、马凯、王学博三位新导演,他们均凭借自己的长片处女作,获得了西宁first电影展、柏林电影节、釜山电影节等不错的奖项。
为此,我们从剧本、资金、演员等方面聊聊,如何开始拍你的第一部电影。
去拍你熟悉的故事
2016年10月14日,《黑处有什么》在院线上映,10天获得600多万票房,这是三年前的导演王一淳完全没预料到的。

这部被称为“《杀人回忆》加《少女哪吒》”的电影混杂着商业性和作者性,并在一众青春片中凸显出独特的气质。王一淳并没有电影专业背景,“也不认识什么电影圈的人”,大学学法语,毕业后在广告公司工作,创过业,但很快回归家庭成为带孩子的家庭主妇。
《黑处有什么》的剧本断断续续写了差不多十年,跟很多导演的处女作一样,它取材于王一淳的私人记忆,“比如说我爸和片中的爸爸很像,是一个小地方的小知识分子,脾气又臭又硬,然后在单位里也不太会来事,和别人的关系也很别扭;我在少女时代也有那么一个很那样的同桌,留级生,爱打扮,和外面的社会青年联系紧密。”
王一淳觉得第一部片子从自己熟悉的故事入手是很好的选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青春故事,“我们这代人这么磕磕绊绊长大,肯定是大家都有一些暂时还无法释怀的东西,这个东西应该就会有一部分共鸣。”
对王一淳来说,熟悉的是自己的青春,对《中邪》的导演马凯来说,则是对恐怖片情有独钟。

成本仅为7万的恐怖片《中邪》把今年first的评委成功吓到,导演马凯凭借这部处女作拿到了本届first电影展最佳探索奖。
2010年,马凯考大学时,报了十四所艺术院校,一个没考上。他去淘宝上买了假证,骗父母自己已经去上大学了。六年后,《中邪》的网络版权被腾讯以几百万的价格买下,并有进入院线的计划,“那你父母很高兴吧?”马凯狡黠微笑:“可他们也知道我没去上大学的事了。”
没去上学的马凯漂在北京,想当群众演员,每天去各个宾馆投资料。结果“差点饿死了”,一连四个月没接到戏。后来跟着朋友去了横店,从“北漂”变成“横漂”,他很喜欢横店,可以看到“博士硕士,扫大街的,然后干电焊的,反正你所有想到的行业的在那里全都能找得到”,在这个小社会里,因为马凯外形条件不错,很快就做小特约,能说上几句台词了,类似“大王,敌军已经攻到城下,我们打还是不打”。
三年后,马凯发现做群众演员很难再往上了,他开始转做副导演助理,负责收演员资料,有一次收到一位60岁奶奶的资料,还没说话,对方就哭了,说一定要选她。马凯在横店看到太多各种不同的人和他们的处境,这让他快速的成熟起来。
他开始大量的看片子,把能找来的恐怖片看了个遍,“我喜欢电影都会看三四遍,后来发现必须研究它的构图、演员的走位、镜头怎么拍。”提到恐怖片,马凯就很兴奋,他喜欢那种看恐怖片时“头皮发麻的感觉”,很多个夜晚,他一个人在家看经典恐怖片,他觉得自己其实是个胆子很小的人,经常被吓到要按下暂停键,“缓一缓再继续看”,正是因为自己能“被吓到”,马凯觉得这样他才知道观众有可能在哪些会被吓到。

《中邪》
跟王一淳在老家河南拍自己的处女作一样,马凯的第一个长片回到了他的家乡山东。为了表现《中邪》里出现的农村风俗“还人”,马凯找了好几个村子找到这样的神婆,纪录片风格的手持摄影让观众信以为真,恐怖气氛由此生发。
先拍些小片实践
“当时每个月只能赚1、2000元,觉得电影离我特别远”,马凯坐在小娱面前,回忆起第一次拍短片是在2012年初,花5000块买了个DV,叫了一帮朋友折腾,受美国电影《鬼影实录》的影响,他准备拍一个名为《横店鬼事》的片子。
陆续存了4万块钱,马凯接着买了个佳能5D2和一些小摇臂,准备拍第二个短片,朋友都嘲笑他“别想那么不靠谱的事”。他一共拍了四个短片,几乎是每次有了余钱就投入到拍片中,拍的全是恐怖片,但都没剪辑和后期,现在还放在电脑里。后面,他用赚的5千块钱参加在北京的栗宪庭电影培训班,上40天课,在一次杨超导演的拉片课中,他觉得“一下子通透了很多”,觉得可以筹备长片了。
直到《中邪》开机时,马凯兜里只有几万块,他的制片人已经是负债状态,两人当时心里琢磨的是拍完“卖个网大”。
刚刚在釜山电影节上,导演王学博凭《清水里的刀子》拿到唯一的竞赛单元奖项新浪潮大奖,而距离他第一部短片作品,已经过去了10年。但其实,《清水里的刀子》这个电影,已经在六年前开始了。

《清水里的刀子》
当时,王学博在上大学三年级,他看到石舒清的小说《清水里的刀子》,甚为感动,和十几个同学一路“杀”到宁夏西海固拍摄了一部短片,吃住在当地农户家,同学也不拿报酬,这部短片的成本“大概六七百块钱”。这部短片在2009年入围了南京的中国独立影像展,这让他结识了当时的评委万玛才旦。
没有钱和人脉,就去赚钱、攒人脉
当王一淳想把写了多年的剧本拍出来时,曾尝试去找资金,但因为没作品也没人脉,碰壁而归。最后她咬咬牙从家里拿出了300万积蓄,现在回想起,王一淳说当时家人都觉得她“疯了”,这300万砸进去,可能连个水花都没有,“我反复掂量过,也为这个事努力了很长时间,不试试可能一辈子后悔。投了,我认,愿赌服输。”
对于王学博来说,筹拍的6年同样是一个找钱、找资源的过程。
毕业后王学博依靠拍摄一些商业短片养活自己,并且开始筹拍长片。开始找资金并没有很困难,《锤子镰刀都休息》的导演耿军给他介绍了部分投资,王学博和副导演马上前往宁夏,看景和体验生活呆了十个月,那是个漫长而难熬的十个月,因为没有青菜吃,一直口腔溃疡。

《锤子镰刀都休息》
在看景时,王学博发现夏天的西海固草生长得太茂盛,但他想要的电影的质感是比较肃穆的,所以一直等到冬天。因为当地风俗和固定的一些观念,这时约好的那些非职业演员都退出了,而当时的王学博并不擅长跟村民打交道。
因为这个意外,这次拍摄计划流产了。这对王学博是个不小的打击,剧本改好了,资金到位了,但还是开不了机。
回到北京后,他开了个影视公司,开始做制片人,最多的时候他一天要见12个人,“我也不是说那种呼风唤雨的大制片人,但是我肯定可以做到把所有的工作全部做得特别细,不会让你操心。”
制片人的经历让王学博在如何制作一部长片上有了更多把握,“制片人的工作对于整个影片的影响会特别大,你找到钱了,你怎么样控制成本,怎么样抓生产,怎么样去销售,怎么样去营销怎么样搭盘子。”
王学博说做第一个长片的经验就是先“就是努力把一个事情做成,不能畏手畏脚”,在给耿军导演的新片《轻松+愉快》的制片人时,“开机的时候一分钱没有,我也让他开了,他拍了43天,我43天融到了钱。”
拍《清水里的刀子》时,开拍的时候钱也不够,然后在开拍之前又找到一笔钱,并请来了尔冬升、张猛、万玛才旦做监制。开公司和做制片人的经验,不仅让王学博在资金上相比其他新导演更充裕,也让他积累了行业人脉和筹备电影的经验。
工期紧、钱少、难找好演员….那就自己都兼着
筹备期只有半个月,正式拍摄30天,王一淳每天晚上拍完“回到酒店一头往床上一扎”,五个小时后起来继续拍。“因为剧组的工作人员都是从筹备开始算劳务的。你筹备期长了跟你拍摄期长了一样。你最大的成本就在那。但我就是希望我拍得从容一些,各种准备能更充分一些。”
为了节省资金,导演、编剧、制片、场务……王一淳一人身兼数职,现在回想起来,王一淳觉得觉得这种分工不明确让她非常痛苦和煎熬,“制片人是管钱的,导演是管艺术的,如果导演动不动跟剧组的人说钱的事就让你的形象挺打折扣、挺分裂的。”王一淳建议在筹备阶段,制片人和导演最好是两个人,各司其职比较好。
为了省钱,王一淳在写剧本时就注意到剧中可能要用到的东西,她全部先在淘宝搜一遍,觉得什么东西能买到再写进剧本,“比如写到过去塑料皮笔记本,我也上网买了几本,还是那种泛黄的,然后还有那种什么小虎队的贴画,甚至当时的老课本,我也上淘宝买了一本。”
但因为筹备期太紧张,在道具上有很多达不到王一淳标准的地方,一场戏中,警察在看一本黄色画报,画报是美术组现场去打印的,“颜色比较暗淡,但可以更鲜艳一些,就那种丰乳肥臀的感觉。这些都是可以通过前期更充分的沟通来解决的问题,甚至就拍摄期如果提前几天检查后几天的道具,也会有改变的机会。”
剧组演员中有一半是非职业演员,还有很多是王一淳的亲戚,比如女主角骑车经过一片荒地时,演正在被埋的尸体的演员是王一淳的表妹,而挖坑的是她的表妹夫。
马凯的《中邪》剧组,则是所有演员都是非职业演员。为了让大家进入氛围,马凯竟然带演员们半夜去坟地体验。“当你进墓地的时候,你站在那的时候,你不敢动。你动的时候,特别的慢。你不会发出任何动静,然后你瞳孔就会放大,脑子特别特别的清晰,所有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那时候血就冲脑,如果稍微有点动静,立马就能晕过去。”

《中邪》
《中邪》里没有特效化妆,也没有恐怖音乐,这些恐怖元素都没有的情况如何吓到观众是非常难的。“我们当时就一起想,这个是比较难的,吓人的全是长镜头,就配合起来特别困难。”
故事发生在一栋远离集市的二层楼房里,因为气氛过于恐怖,剧组成员都不敢一个人待在二楼,在一场上吊戏中,女主角“死后”不敢一个人呆在屋子里,只好安排另一个男演员在屋子里陪她。
有一场戏,“女鬼”杀人,“血”会溅到衣服上,但因为经费有限,只有这一件衣服,所以这条戏只能拍一次。剧中男主角拿的拍摄机器重达20斤,为了这个长镜头,他一共拿着机器排练了30多次。
非职业演员的本土化气质和电影本身的伪纪录片风格浑然天成,这也是《中邪》成功的原因之一。对于如何调教非职业演员,马凯觉得:“选择这种非职业演员,是看中了他身上的气质,那种生活习惯那种感觉,你不要过多的去调教他,你的目的达到就行,不要给他太多的框框架架,这样你会改变他原有的那种东西。”
再次回到西海固拍戏的王学博开始适应那里的恶劣天气,《清水里的刀子》启用的也全是非职业演员,准备了那么久终于开拍了自己的处女作,王学博感受颇深:“你可以用两万块钱拍一个小片花,你要有你的冲动和行动,这个才最能感染你身边的人。他们会看到你的东西有价值和前景,才会有信心跟你合作。”

《清水里的刀子》
不是结局的结局:他们都有了下一部
从制片人转做导演,虽然有点“曲线救国”,但在釜山电影节上的大奖对王学博来说,是个极大的鼓励。现在,王学博开始招募演员,准备拍第二个电影了。
《黑处有什么》的结尾,小女孩走进一片芦苇丛中。在一个点映场中,一个很有名的电影导演替王一淳可惜:“这本来是个很好的镜头,为什么最后没有把镜头摇开,无边的芦苇,意味着无边的黑暗啊。”王一淳笑着说:“就那一小片芦苇,往哪里摇,再摇就穿帮了。”
因为没有钱做后期,电影拍完后在家里放了一年。直到在first电影展的一个活动上,朋友让她试着申报一下。最后拿到了first电影展最佳导演奖,入围了入围过柏林国际电影节新生代竞赛单元、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最后被和和影业买下,进入院线。
当时投完电影节后,王一淳心里想:“我想着这辈子跟这个事没缘了,我该努力也努了,该试也试了,我安心在家带孩子了。”主妇就先不做了,她已经开始筹备下一部新片。
“在7月20号之前,我一无所有,我还欠了一屁股债,三四万,你知道对一个月赚一千多块钱的人,欠三四万是什么样的概念。我几年才能还清。但是现在就是屌丝逆袭。”马凯在接受完小娱采访的第二天,他又回到了横店,“北京太浮躁,不能静下心写剧本,我还有好多想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