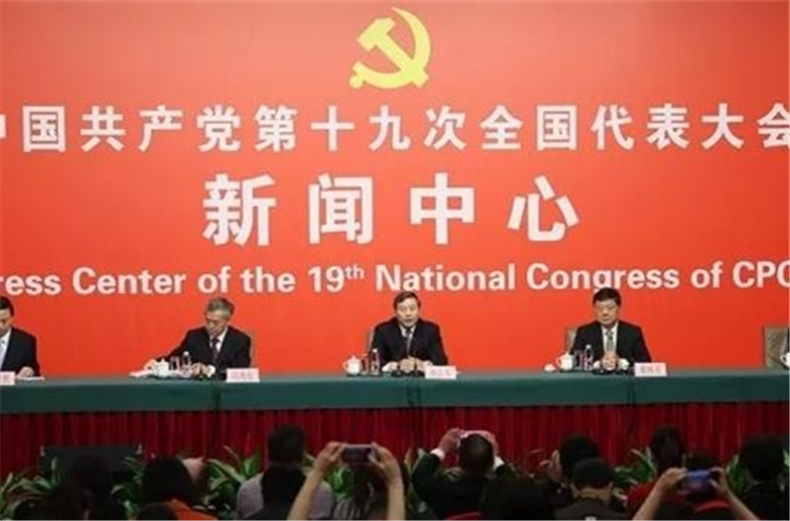成立于1957年的上海电影技术厂迄今已有近六十年的历史,隶属上影集团,是国内最早建成的专业化电影洗印基地,也曾是中国年产量较高的影片技术加工基地。其中负责胶片生产的洗印部门,是这个厂的核心生产部门。如今,技术厂传来消息,将于十月底前关闭最后一条胶片生产线。

上海电影技术厂
随着人们脚步的加快,那个属于“从前慢”的时代的事物也正一一离我们远去。作为一门十分年轻的艺术,电影的每一次革新,都伴随着技术的进步。新技术的流行,总是宣告着老技术的淘汰。而随着数字技术的井喷式发展,在人们为VR技术和CGI特效惊叹的同时,曾在电影领域长期制霸的胶片,也将退出历史的舞台。
从柯达倒闭开始,胶片将死的言论从未停止过。伴随着上影厂胶片生产线的关闭,加上之前就已经关闭胶片生产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电影洗印录像技术厂,这一次,胶片电影在中国可能真的要消失了。
生产线从鼎盛到关闭不过十几年
数百年来,影像的世界一直以胶片作为时间轴,胶片也见证了电影的发展史。从黑白到彩色,从8毫米、16毫米,到标准的35毫米甚至70毫米,人们通过一卷卷胶片,不断追求还原世界的最大可能。
胶片也没有辜负人们的期望,通过不断的技术改良和工业沉淀,以其优秀的感光度和迷人的画质促进着影像的美学和表达能力不断发展。
近年来,使用胶片拍摄的电影已经越来越少。在华语电影世界,除了香港、台湾地区还有《一代宗师》、《聂隐娘》这样的名导演大作,大陆也只有《箭士柳白猿》、《长江图》等寥寥无几的胶片作品。

《一代宗师》海报
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源地。作为老牌电影公司的上海电影制片厂,是近代中国电影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生产出《铁道游击队》、《牧笛》、《南征北战》、《鸡毛信》、《渡江侦察记》等经典的老电影,《建国大业》、《东京审判》等新世纪的主旋律电影,也从这里走出去。
这些电影虽风格迥异,但有一个共同的标签——胶片电影。
不管是技术上的辉煌,还是胶片市场的火爆,都曾为电影制片厂带来了巨大的产业效益。
上海电影技术厂现任厂长陈冠平告诉记者:“我们厂是国内最早建成的专业化电影洗印基地,也是中国年产量较高的影片技术加工基地,曾有太多经典电影在这儿诞生。《生死抉择》、《2046》之类的,大家应该都知道。当然也有很多进口分账大片的拷贝洗印,都是我们做出来的。”
本次上影厂将要关闭的,是原来厂里做胶片工作的核心部门——洗印公司。既然是个厂,就得看生产的量。
在陈冠平看来,中国电影最辉煌的时代,始于市场化之后。随着胶片电影市场的繁荣发展,洗印公司的产量不断提升。最辉煌的时候,是在2002-2010年之间,车间曾出现过八条生产线全开以及上百名工人同时操作的盛况。
随着数字技术的日臻成熟,胶片时代极盛之后的衰退如迅雷般猛烈。2012年是一条分水岭,在此之后,胶片业务出现了断崖式下滑。从生产线停产过半到如今的全线关闭,仅用了四年。
被问及胶片没落的问题,陈冠平说:“这一切也是无可奈何,谁也没有办法。无论是人力成本还是设备损耗和环境能耗,如果按照之前一年两三千万的收入,还可以维持基本运营。对于技术的发展,企业要面对市场化的竞争,在目前国内胶片电影毫无市场的情况下,真的无法继续运行了,目前我们将全线转入数字制作。”
记者询问生产线关闭后设备和工人去留的问题,陈冠平表示,“设备应该就留个两三台。但是厂里要给这些为生产线奉献了整个青春的工人们一个体面的结局。他们从二十岁左右就到这儿来,在这儿工作了三四十年,见证了技术厂的成长。我们很感激他们,一定要让他们体面光荣地走出这个厂。”
随后记者在车间也看到了将要停用的洗印设备,却被告知“虽然这些机器能保存下来,但是长时间冲印胶片,里面残存了很多化学药物,一旦停下来,不出几个月就会失去生产功能,也就没有冲印的能力了。”
在冲印车间,记者见到了依然在这条最后的生产线上工作的60岁老工人钱顺安。他从年轻时在技校学了技术就来到这里,已经做了近39年。
忆起当年的鼎盛时期,依然有些小激动,“大概2009年的时候,订单非常多,我们周六周日也不休息,连续地三班倒,甚至一天工作十二小时,还是根本忙不过来。那会儿,这里热闹得不行。”
被问到老人所在的生产线现在的情况时,钱顺安十分感慨:“现在这条生产线就剩三个人了,生产的也不是电影,就是一些民营公司送来的玩具幻灯片订单。等过几天这里的库存胶片用完了,我们的工作也就结束了。”
胶片没落的必然
数字技术刚出现时,所呈现出的影像还是极其粗糙的。虽然比起胶片,更廉价也更便捷,但总体上还是完全无法与性能几乎被挖掘到极限的胶片相比。
但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这个差距已经越来越小了。技术厂的技术工人告诉记者,“随着数字影像技术呈现井喷式地发展,无论是传感器面积,还是分辨率、动态范围等技术越来越接近甚至达到了胶片的水平后,胶片必然会被淘汰。”
当然,胶片的终结不只是技术上的必然,还有经济上的考量。2002年,美国七家大制片厂联手成立了数字电影倡导组织,该组织的使命是“建立和记录数字电影开放式体系结构的推荐规范,确保统一的、高水准的技术性能、稳定性和质量控制”。
在数字电影的历史元年1999年,《星球大战前传:幽灵的威胁》在美国首次进行数字商业放映时,电影采用了基于TI公司数字光学处理芯片技术的放映机。从此,电影的信号就具备了直接进行数字传送和放映的可能。这也意味着,电影发行中的拷贝复制、储存、回收等巨大发行费用,能减少90%。
数字摄影最大的优势即胶片的劣势,在于其迅捷、轻便和廉价。以前拍摄一部电影,耗费的胶片是一笔很大的费用,一般导演、剧组承受不起太多的拍摄条数。
胶片电影时代,拎着沉重的胶片拷贝疯狂赶路闯红灯,是每一个发行跑片工作人员的真实记忆。
在胶片时代,一部90分钟的电影制作成胶片拷贝,胶片长度近3000米,需5至6本拷贝,每个拷贝的重量可达25公斤,价值近万元。若有紧急任务,甚至要连夜坐飞机送拷贝。
IMAX胶片放映系统诞生后,体积庞大,程序复杂。放映《阿凡达》、《变形金刚》等商业大片时,其片盘直径近一米八,加上胶片重量将近800斤。放映时,需四个片盘同时动作。普通放映员要上岗,需提前学习一个月,经过无数次实践后,才能保证每次放映成功。
在胶片时代,对电影发行人员、放映人员来说,送拷贝、放电影,都是责任重大的工作。但伴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如今的数字拷贝,只需一个小小的U盘,即可快递至各大影院,方便快捷。无论发行人员还是电影放映人员,再也无需担心胶片丢失、放映卡顿或出现损坏。
最后的胶片电影《长江图》
不久前上映的电影《长江图》的导演杨超,也许是眼下对于胶片拍摄最有发言权的一位。当胶片质感中细腻呈现长江上氤氲的雾气随着水波散发出关于生命和历史的拷问时,这部电影也被冠上“中国最后一部胶片电影”的落寞定语。
3500万,对于一部文艺片来说,称得上是“耗费巨资”。而这些钱,都与胶片脱不了干系。胶片给拍摄工作带来了巨大的麻烦。由于拍胶片的时候看不到最终的效果,只有很模糊的模拟成像的影影绰绰的影子,导演只能看大概的构图和表演。因此,现场的一切工作,结果都是未知的。
“和最终4k的成片比,现场看到的大概只有1%的效果。这种未知感带给导演、摄影和全组人巨大的期待,有一种把工作成果交给老天爷的感觉,有种仪式感。”杨超说。
也因为这种未知感,拍胶片使得线索非常繁琐,需要多次拉皮尺来测量焦点。数字摄影师在监视器上用眼睛就可以判断,胶片需要在走位、排练、实拍前多次测量镜头与实物的距离,这需要花费很多时间。
灯光师需要完全凭借自己的经验,现场看不到光影效果,还需要不停地用测光表测光。这个必须靠经验直觉和本能去感受,对从业人员的要求很高。
此外,胶片的摄影机非常重,移动起来很累。每次摄影机的移动都是一件大事,高机位的吊臂也必须是最大尺寸的,普通的吊臂无法承受胶片机的重量。
除了拍摄,送样片、初剪的工作也更为周折。杨超告诉记者,拍摄的过程中,每拍完一卷,换片员要把片子换下来,“换片的过程也很神奇。换片员会用一个只开了两个小口的暗袋把机器套住,全凭手感把片子从机器上取下来,再装进一个金属密封的盒子,再用胶带封住。全程不能有一点透光。每次换片,换片员手上都承担了全组人的工作成果。”
拍完的片子叫熟片。拍完后就把熟片放进船上的大冰箱里保存。之后存到两个大行李箱,送片员会带着行李箱下船,搭乘最快的交通工具去机场,再买最早的机票回北京。两个行李箱就是他能携带的最大量。
胶片到达北京后,事先联系好的洗印厂会尽快完成冲洗。底片经过转磁,磁带再转成数字文件,送片员再带着硬盘回到剧组。导演和摄影师就检查拍的东西,看看有没有问题,是否需要重洗。如果没有问题,这一轮送片员的奔波就算结束了。他回到剧组等待两个行李箱再次装满,再送去洗印厂。
拍摄的三个月,送片员就一直处于这样的奔波状态。
而硬盘里的影像被导演看到时,跟最后的成片仍有很大差距:“最后出DCP(Delivered Carriage Paid,数字电影包)审片的时候,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拍摄成果。拍胶片就是这样,从拍摄到最后后期的全过程,都不知道拍成什么样,都是经验的估算。”
而这一切,在杨超看来,“都使得拍摄更庄重。数字现场就知道现场效果,剪的时候也是完全掌控的感觉。胶片使全组人处于期待之中。”
用另一部难能可贵的胶片电影摄影师李屏宾的话说,就是“胶片更接近于创作,因为有一部分完全交付给未知的命运了”。
《长江图》其实并非一部完全以胶片拍摄的电影,还有20%是采用数字和DV拍摄,这个原因说来无奈:“第一期拍摄结束后没钱了,又继续融资,开始第二期拍摄。中间隔了一年多,洗印厂已经倒闭了,就只能用数字来拍。”
可以说,这部“最后的胶片电影”,用亲身的经历,见证了胶片时代的终结。
胶片退出历史舞台,胶片的美学不会消失
如果今天开始拍《长江图》,恐怕杨超和李屏宾也不会选择胶片。
“今天的数字拍摄技术,已经完全可以实现胶片的效果。但在2012年那会儿,胶片所能呈现的明暗过渡的层次,它的敏感度,是数字达不到的。”
对于老工艺和传统技术的消失,杨超说:“会有一点情感上的怀念,但谈不上伤感。数字已经完全可以达到胶片的质感,反而带来了更多的便捷。胶片介质的消失是健康、自然和顺理成章的。”
杨超认为,胶片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胶片的美学不会消失。那种多层次、复合的、缓慢变化的质感以及美学的观念,会在数字的自由度中继续保留下来。数字带来的自由度并不会影响美学。对于真正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创作者来说,数字反而会带来更大的可能性。因为技术是没有止境的,而美学是一种限制。影像创作者找到自己的角度,找到自己的美学表达观念,就不会被技术伤害到。
虽然胶片的生产停止了,但至少在今日,胶片仍有其无法取代的优势。
首先,在数据保存管理方面,如果是一部常规时长一个半小时的电影,要用数字技术保存的话,需要15TB至120TB的储存空间。除了对空间需求巨大之外,存储技术仍不够成熟也是重要的难题。目前,一旦存储设备损坏,数据就会丢失。但胶片就不存在这个问题。胶片除了是拍摄格式也是储存格式,而且正常情况下常规的胶卷可以保存数百年。
而胶片最主要的优势还是在成像方面。胶片能够更加细腻真实地体现被摄场景的细节和氛围。虽然有朝一日,数字技术一定会超越胶片。但目前胶片除了人们最常提到的颗粒感属性之外,依旧“凌驾”于数码之上的几个属性包括:宽容度、随机像素、色彩、光线变化、影调等。胶片包容的程度要比数码高。
拥有这些优势的胶片,虽然在快速发展的国内电影市场因为其不便性已经逐渐销声匿迹,但在已经成熟的国外电影市场仍有一席之地。
如今在国外,胶片仍然有自己的一方乐土,还是有不少商业大片依旧使用胶片拍摄。昆汀·塔伦蒂诺和克里斯托弗·诺兰两位极具个性的导演都是胶片的坚决拥护者。而且他们坚决只用高规格胶片拍摄电影。
诺兰使用65毫米IMAX胶片拍摄《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盗梦空间》与《星际穿越》,并以70毫米IMAX胶片格式上映。昆汀使用潘那维申超70毫米摄影机和65毫米胶片拍摄《八恶人》,并以70毫米胶片放映。
在他们看来,胶片不仅是一份情结。相比用数字去模拟“胶片质感”,不如用真正的胶片来摄制、放映。正如昆汀·塔伦蒂诺所言“电影若不能以35毫米的胶片形式呈现,那人们不过是在电影院中看电视。”
诺兰、J.J.艾布拉姆斯、昆汀·塔伦蒂诺对胶片技术的延续做出了实际的努力。他们与同自己合作紧密的大片厂进行谈判,要求片厂每年购入一定数量的电影胶片用于拍摄,以维系胶片技术的生命力。
此外,国外的胶片修复也有很大的市场,这也为胶片技术的延续增加了新的活力。
胶片电影生产停止,但老胶片的修复仍在继续
当然,随着技术的发展,不仅是电影行业,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发生变化。
无论是微信取代短信,支付宝取代钱包,只要技术的发展在继续,就总会有被淘汰的旧技术。事实上,不仅是作为终端的胶片无法逃脱离开历史舞台的命运,近日已有关于最新的苹果手机可以取代单反相机的言论。虽然还不能完全实现,但是也证明了每一种技术都在日新月异地推陈出新。
随着VR技术的到来和拍摄设备的更加便捷精密,拍摄电影的门槛将变得更低,人人是导演的时代就在眼前。电影的未来无疑将更加广阔,无数新的商机也正在涌现。但是如何在愈加便捷的技术条件下,保持对艺术的“工匠精神”和敬畏之心,仍是这个时代的难题。
不过,虽然胶片生产线将停止工作,但是上影厂的胶片修复工作依然正在进行。每年仍有相当数量的老电影胶片被送到这里来修复,并且会对老电影的拷贝进行保存。
上影厂修复工人胡玉娥告诉记者:“我在这里工作了三十多年,从早期的胶片剪辑工作转型到现在的修复,虽然工作内容变了,但是我们的工作态度不会变,力争让这些可能逝去的老电影重回观众的视野。”

2016年9月20日,上海电影技术厂,修复底片师胡玉娥正在检查底片。
谈到未来的发展时,陈冠平说:“虽然胶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凭借之前积累下的良好诚信和优秀品质,我们仍梦想着能够重现辉煌和恢复市场地位。最重要的是,我们依然留存着这样一份工匠精神。无论技术如何变化,我们都将带着初心去做每一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