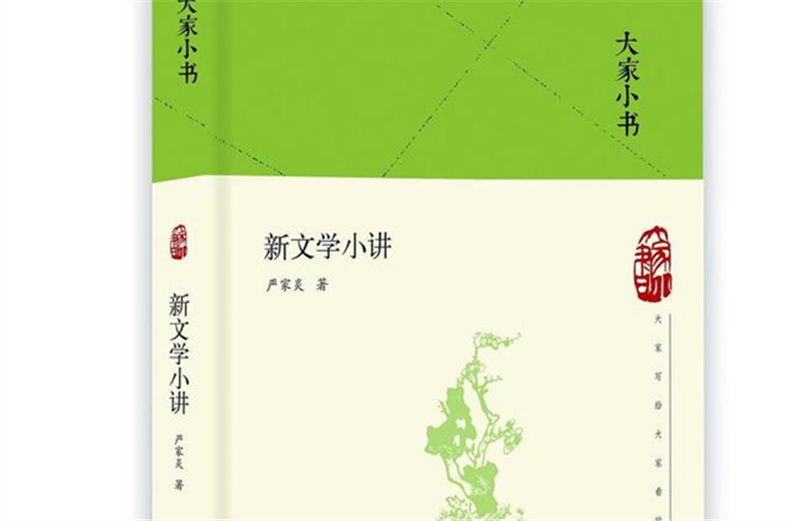天下的读书人太多,书也浩若烟海。杨典说他最爱读的乃“无人读过之书”。
杨典是这样解释的:所谓“无人读过之书”,并非举世从无所见,而是指一时被忽略,或因年代久远,或因译介缺失而暂时难得一见之书。
杨典的读书品位,向来如此。十余年前,他就写过《孤绝花:绝版书评肆拾捌》。听这书名,知其刁钻矜贵。杨典最近又出了部类似的集子,叫《巨鲸:私人文学史》。有句说:“其中常有隔世滋味、孤绝气息,毫无当代眼前出版物之人间烟火气。”
杨典所负的才学,琴棋书画诗酒花,大抵都是无用功。我有时想,他合该活在晚明,若早些,魏晋也可,或南渡的宋,迟了一步,就清末民初吧。那些垂垂危矣的时代,颓唐的不甘,乜斜冷眼,携几箱卷册,一把古琴,披发入山林。我也庆幸他活在当世,在靠着商业图书、肥皂剧本、报刊杂文谋生之外,还在自觉的疏离之中保持着自己审美的格调。
杨典素喜古代笔记,认为“在其保留浩瀚之精髓时,还能纤毫毕现,不失细节”(《鹅笼记》序),更以“炼字”为旨,先后撰写《随身卷子》《懒慢抄》等百衲本现代版“类书”,亲身复古“笔记志怪”这一遗失的文学体裁。
《巨鲸》三十二篇,起笔《说药:从古代志怪笔记看中西医学之别》。杨典从宋人话本出发,上溯《黄帝内经》,下至《本草纲目》,旁涉不止中医,远及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体解剖、欧洲早期医学的“胆液论”,皆从书中得来。天文地理,芜杂遍野,性好复古却非守旧,在中西融汇触类旁通后,文字里常有一些荒诞派的气味,甚或后现代的迷雾,古今一体,漫笔纸间,最难得,始终少年意气。
《说药》之后,跟着几篇谈日本文学:小泉八云、一休和尚、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大江健三郎。20世纪即将结尾的最后几年,杨典在日本,早年的回忆录《打坐》里说过,他曾因做一份擦洗高楼玻璃的工作,而挂在关东一些城市的高空,长达几小时。那份工作的感受想必与他当时接受的日本美学思想一起进入了他的血液。杨典读书,我读他写的书,读出了“色空”与禅的精神,把握现世的欢乐,遵循自己的内心,终归无涯,如梦幻如泡影。
杨典生于1972年,他的少年岁月浸染着俄罗斯文学和拉美文学的色调。吉皮乌斯、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和新近些的波拉尼奥。他们都有一种强大又敏感的气场。这些书和作家造就了一个人的青春经验和记忆,如影随形陪伴漫漫人生。在杨典最爱读的书里,位列第一的就是这些“可终身反复诵读的书”,每一次读,都有新的领悟,而这些大部头的经典作品,尽管在现代仍然流通,真正仔细阅读的人恐怕也不多,仍可归入“无人读过之书”。
《巨鲸》的其他篇目,有一些是淘旧书所得,自有读书人都懂的一番欢喜。其余最多的,是民国文人作品。比如,梁启超的《陶渊明》、喻血轮的《绮情楼杂记》、袁克文旧作及《寒云藏书题跋辑释》、陈巨来《安持人物琐忆》《吴宓日记》等。也是“捡漏”的读法。说起鲁迅的处女作,我们常以为是《狂人日记》,其实是一篇叫《怀旧》的文言文小说,最初发表于1913年4月25日上海《小说月报》,杨典就此展开对鲁迅的误读以及鲁迅出版的复杂性的论述。杨典对《绮情楼杂记》评价极高,将这本书比之为“黛玉的血泪”,点点滴滴,无时不流,无漏不尽,并且以为这种带着挫骨扬灰、肝肠寸断亦绝不后退的“觉有情”而忍受之长痛,是比关老爷刮骨疗伤更具神性和耐力的事。论可存榷,可见襟怀。
书名《巨鲸》,取自于波拉尼奥和俄罗斯文学的部分。现在很少有作家愿意挑战这么大的规模,也很少有作家具备写作“巨鲸”所需要的艺术、历史、音乐、科学等通才能力,以此为全书题眼,以“私人”性加以定义,杨典的气量和才具,也是有向着大海而去的想法了吧。
那些巨著的鬼魂,终究会“像哈姆雷特父亲的鬼魂一样回来打扰我们”,杨典如是说道。
作何:林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