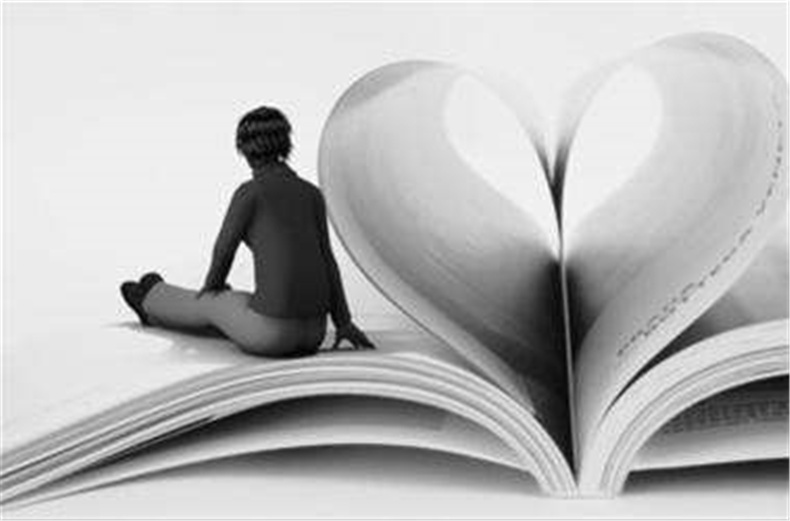近些年,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以集部为研究对象的趋势,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魏六朝集部文献集成”的立项,到“集部文献整理之经验与问题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再到以“集部”为主题的文献丛刊、古籍整理、学术专著及研究论文的出版发表,都预示着对集部的研究日益引起学界重视。从具体实践到理论提炼,集部成为拓展古代文学研究边界的重要视角。
聚焦文学典籍
长期以来,古代文学研究主要围绕作家作品展开,包括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两方面。而集部的研究则更多关注作家作品集的形式载体问题,在此层面,集部的确赋予古代文学研究另一番景象和视野,但学界也需对集部研究的范围和学术宗旨有清晰的认识。前者界定集部研究的对象和内容,不宜与古代文学既有研究范式有过多的“纠缠不清”,集部研究要有相对固定的界限,否则便失去了自身的意义;后者则要求集部研究宜避免“自我封闭”,其宗旨还是要回归文学史的本位,否则集部研究的价值意义便无从体现。
集部是传统目录学中有关古籍分类的四部体系之一,指涉的是文学古籍的范畴,著录的载体是书册形态的典籍。这意味着集部的研究首先关注的是文学典籍即作品集,这与文学史关注作家作品有所不同。当然就研究范围而言,文学史较之集部更宽泛,如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史要关注《世说新语》《搜神记》,甚至还要涉及《水经注》《颜氏家训》和《金楼子》等,但它们都不属于集部典籍。因此,集部视角实际上“缩窄”了文学史的范围,但集部里的有些文献也是文学史较少关注到的,如尺牍、奏议等,主要是具有实用功能的应用文体。简言之,集部与文学史的范围既相互交叉,又有所区别。
集部研究主要是处理文学典籍,即作品集。这些作品集是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的载体,两者之间呈现为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传统文学史体系的主要内容是在概述作家生平之外,对文学作品作出评价,包括其思想意义、艺术属性等,两者的组合决定了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中的地位,这实际上是文学成就史的书写模式。20世纪下半叶出版的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还有作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的袁行霈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都采用了这样的框架结构。尽管学界曾有过“重写文学史”的热烈讨论,但并未从根本上撼动文学史的固有书写模式。这种文学史书写模式很少对作品集进行关注和阐发,作为文学作品载体的作品集并非文学史叙述的主体。笔者认为,集部研究应着眼于这种文学史书写模式的缺位,并加以弥补和开拓,这也是集部研究得以成立的主要依据之一。
当然,也不宜渲染夸大集部视角的研究,除传统的对作品集的校注整理外,古代文学文献学其实也包含集部范畴的研究,如曾枣庄的《集部要籍概述》、祝尚书的《宋人别集叙录》、刘跃进的《玉台新咏研究》和傅刚的《〈文选〉版本研究》等。最近几年“集部”意识凸显,也有学者尝试从学科体系建设层面展开研究,如卢盛江的《集部通论》等。这都为包括作品集在内的集部视角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值得借鉴。
调查作品集版本
集部研究主要表现为对作品集的关注和探讨,所以,开展集部研究可首先在古籍层面进行作品集版本的调查。研究作品集,不宜只盯着今人的整理本,而是需要到积蕴深厚的传统文化典籍里找根基,为研究奠定坚实的文献及学术基础。作品集的版本调查,包括作品集的存世版本和注释研究类著述两种。如贾谊集,存世有明成化十九年(1483)乔缙刻十卷本《贾长沙集》,即属集子的版本;而清人夏炘的《汉贾谊政事疏考补》,则属于学者有关贾谊作品的研究类著述。一般而言,调查的古籍时间下限在1912年,但也可酌情延伸至民国时期。
通过版本调查,可以在单纯的作品集之外获得大量一手文献资料,如序跋、批注、评点、资料辑录及其他各类形式的前人研究成果,既可吸收已有学术积累,又能开阔研究视野。例如,前人的手跋和批点,特别有助于深入理解作品文本,但在今人整理本作品集中,是基本看不到这些细节的。因此,要利用好但也不应满足于整理本,充分利用整理本之前的文学古籍无疑可以开拓更多研究空间。古代文学界曾存在一些声音,如认为研究处于瓶颈期,不容易找到新的选题,存在大量重复性选题而缺乏原创性,有些研究流于碎片化等。但如果遥望古代浩瀚的文学典籍,哪怕是经典作家的作品集,都可能发现很多被遮蔽的文学史料,或许从中能够找到新的研究突破口。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看待史料的眼光。
重视叙录撰写和个案研究
作品集的版本调查,是为版本叙录和个案研究两项内容服务的。叙录是自西汉刘向以来文献整理的固有环节,形成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叙录范式。以作品集为主要内容的集部研究,要重视叙录范式下的作品集叙录(或称“提要”)撰写,以确立集部研究的文献学基础,发挥其为研究者提供导引的学术意义。如调查汉唐作品集在宋代的存佚及流传状况,绕不开《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两部叙录著述,这就是旨在记录典籍基本状况的叙录的学术价值。
个案研究包括作品集的编撰过程及系年、版本系统与流传、编辑体例、成书层次和内部文本特征等多方面内容。其中的成书层次指确定作品集在成书链条中所处的节点,进而确定文本的地位。汉魏六朝别集在这方面有突出的表现,据南朝梁阮孝绪的《七录》和《隋书·经籍志》著录,这些别集绝大多数在南朝时期便有传本,但并不意味着现在所见的集子仍保留了南朝传本的面貌,实际上这些集子很多是重编本。经过对存世版本的考察和研究,汉魏六朝别集的成书主要存在六朝旧集、宋人重编之集和明人重编之集三个层次,这牵涉到如何认识集子里的作品文本地位的问题。如陶渊明集,依据现存最早的版本即宋代明州刻本的文献特征,可确定其承自北齐阳休之的编本,即属六朝旧集的成书层次,至少它的主体没有在唐宋时期被重编过。
内部文本特征指根据存世版本的卷帙、篇目、文字及版式等特征,确定作品集的底本来源、成书状况及作品真伪等。如陆机集现存有清影宋抄《晋二俊文集》本,据书中《演连珠》“臣闻禄五臣本施于宠”句窜入“五臣本”三字,可确定是宋人的重编本,绝非承自南朝时传本。再如,鲍照集现存有清初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据小注与唐李善注引者基本相同,及遗留的“愍”字阙笔,可确定宋本鲍照集的底本源自唐写本,作品文本的真伪也由此厘清,因为《四库全书总目》曾怀疑鲍照集“因相传旧本而稍为窜乱”。
更新文学史书写
集部研究未来可能会与文学史研究实现文献共享和观念互动。集部研究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回归文学史本位,自觉以文学史为观照,或推动文学史的新书写,或扩大文学史的界面,或解决文学史中存在的问题,如此方可更为充分地体现其价值意义。如作品集存世版本的调查,最终是要勾勒和描述作家作品的文学影响力及其消长,因为版本不是孤立的存在,密切关联着作品的接受史与阅读史,一部从未有过版本刊刻的作品集很难说有文学影响力。
再如,围绕作品集版本的研究,也会更新对作品的认识。举例来说,存世宋刻本曹植集属宋人重编之集,而集子所载作品篇目超过《三国志》曹植本传记载,这印证了宋人重编过程中增入了一定数量的作品,因此不排除伪作的存在,《郡斋读书志》对此也有揭示。所以,文学史在评价曹植作品时就要有所保留。存世明崇祯间潘璁刻本阮籍集,收录了其他版本的阮籍集未见的四言《咏怀诗》13首,从而印证了这些作品的可靠性,文学史应增加对阮籍创作的四言《咏怀诗》的评价。要之,集部研究在彰显自身学理性的同时,也可修正、补充或影响文学史的表述。
文学史研究能否取得突破,除需要理论观念的推动外,也需要文献材料的支撑。建立在文献学基础上包括作品集在内的集部研究,或许能成为撬动文学史固有书写模式的杠杆,从而与文学史共同形成古代文学研究颉颃齐飞的双翼。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