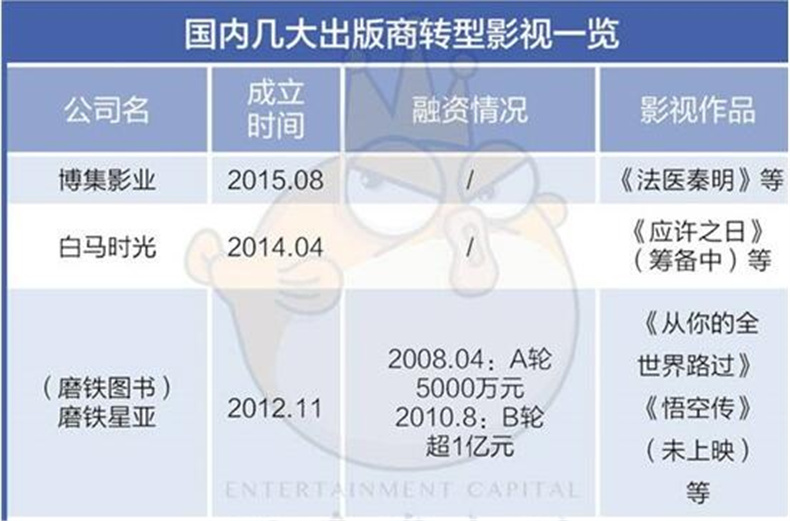汪曾祺是大作家,然而他又是“小”作家。从作品体量上讲,他没有写过长篇小说,也没有文学理论研究的“大部头”;无论是短篇小说还是散文,他的作品没有宏大叙事,都是家长里短的琐事;小说中的人物不是达官显贵,尽是那些平淡的小人物。其作品看上去漫不经心,却彰显出一种文学的境界和价值追求。
其实,对于文学创作的方法论,汪曾祺有着长期的思考,不过这些思考散布在他的书评、随笔和杂谈之中。新近出版的《汪曾祺的写作课》,全面体现了他的文学创作观。阅读本书之后,再欣赏他的小说作品,就会发现他的文字如同老酒,醇香悠远,蕴藏万千气象。
汪曾祺生于传统士大夫家庭,从小受诗书字画熏陶,抗战初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师承沈从文。汪曾祺少年时代开始写作,但是真正的小说创作爆发期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之后,《受戒》《大淖记事》《异秉》等短篇小说广为传阅。他的小说创作不多,却均被奉为文学经典,这种现象其实并不多见。他的作品,有百年历史,有五味三餐,循着中国人的记忆,深植在现实生活之中。
《汪曾祺的写作课》精选了关于阅读与写作的文章35篇,包括对阅读的经验之谈,如《开卷有益》《谈读杂书》《读廉价书》等;对技巧的精确提炼,如《思想·语言·结构》《小说技巧常谈》《文学语言杂谈》;对创作的深刻感悟,如《小说创作随谈》《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的自己》《我的创作生涯》等。文章中干货满满,金句频出,此书对于文学创作者而言,就是一部生动的“教科书”。
作为沈从文的弟子,汪曾祺写作深受其影响。不仅如此,他还认真研读沈从文的作品。本书中收录的首篇文章《沈从文和他的》中,汪曾祺在解读《边城》的同时,表达了文学创作见解。沈从文的《边城》在文学史上地位不言而喻,汪曾祺说这是“一首近七万字的长诗”。这一句话,分量是极重的。小说的语言有诗意,是对一个人文学修养的极大褒奖,而小说中的故事富有诗意,那就是一种文学高度了。
在《思想语言结构》一文中,汪曾祺“正经”地表达自己小说写作的一些看法。小说最重要的是什么?估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在他看来,小说最重要的莫过于思想。这个思想,是写作者自己的思想,而不是别人的思想,也不是哪本经典著作中引申出来的思想,而是作家对生活的独特感受、独特思索和独特感悟。
对于小说的语言,汪曾祺认为,语言一方面承载着小说本身,另一方面小说也是语言的艺术。语言表现内容,内容依赖语言。另外,语言和思想交融,无法把两者剥离开来。语言不好,小说必然不好。语言的粗俗就是思想的粗俗,语言的鄙陋就是内容的鄙陋,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语言主要有内容性、文化性、暗示性和流动性的特征。在他看来,作为小说家,书面语言要少写,语言要贴着生活,要在方言和民间文学中寻找语言的滋养。《我的创作生涯》一文中,他写道:“语言要有暗示性,就是要使读者感受到字面上所没有写出来的东西,即所谓言外之意,弦外之音。”
要想写出好的小说,阅读是必不可少的功课。对于如何阅读,汪曾祺有自己的体会。在《开卷有益》一文中他谈到,作为文学爱好者,应该博览群书,但是也要有所侧重、有所偏爱。一个作家应该认识自己,知道自己的气质。而认识自己的气质,就是看你喜欢读哪些作家的书。书和人是有缘分的,怎样的气质,就选择怎样的书去阅读。在他眼里,写作者读书不能仅仅只读文学书,文学之外的书也可以多读一些。在《汪曾祺的写作课》一书中,他对于小说技巧、散文写作法、中国戏曲与小说的关系、民间文学的价值等等,均有独到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