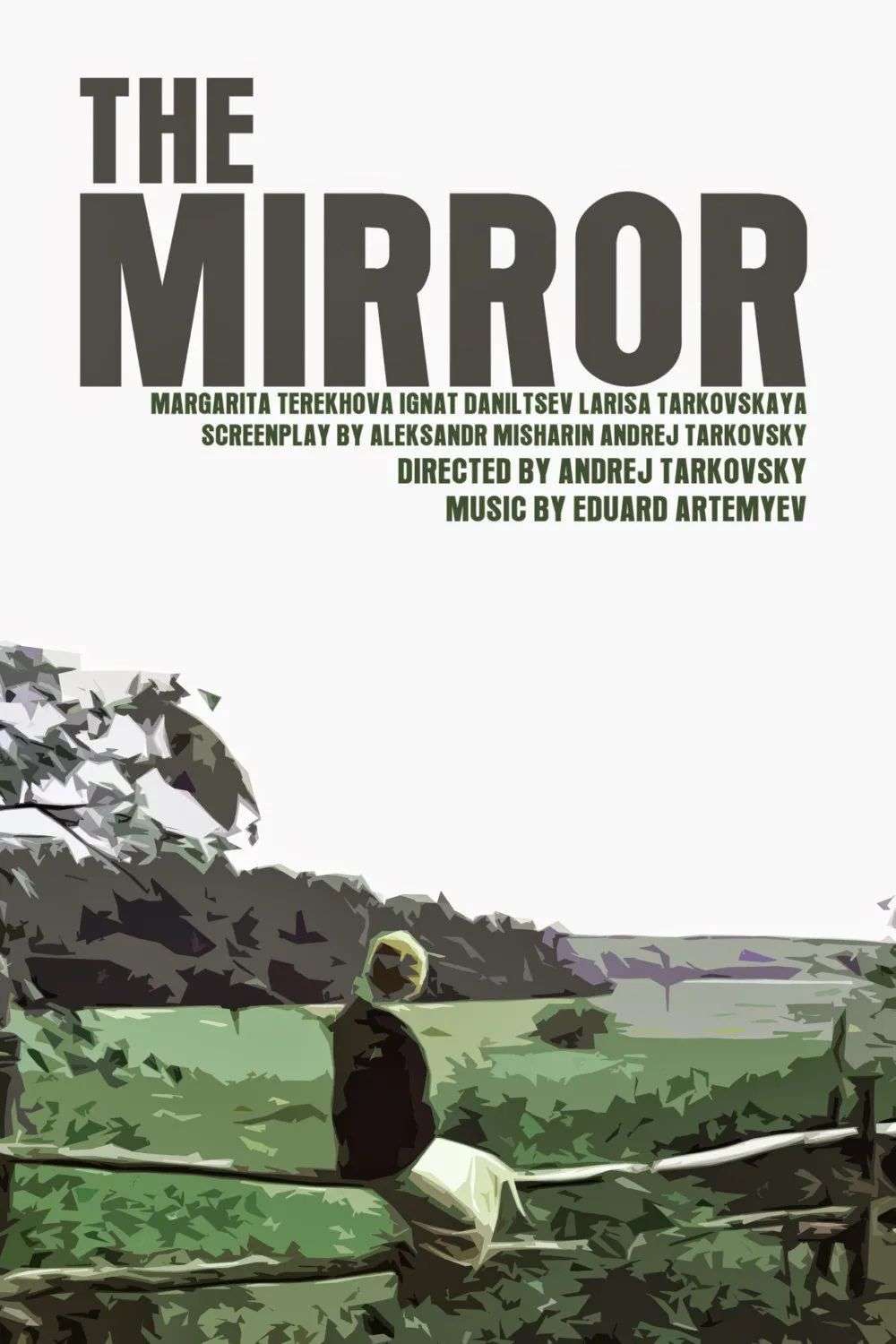“说到电影,这个采访时间不够长了。”《乐队的夏天》中,五条人的仁科、阿茂是讲一口海丰方言的吟游诗人,是在歌曲中拼凑城中村生活碎片的小镇青年,观众被他们那一股“知识分子气息”的赤裸真实所吸引——而近期爆红的一次采访,则让很多人注意到了他们的另一重身份:骨灰级影迷。
音乐之外的仁科,热衷于观看戈达尔、特吕弗、库布里克等大师的作品,阿茂也有一串长长的片单:《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南方车站的聚会》《阳光普照》《热天午后》《雁南飞》《绿鱼》……透过这些片单,很多人也终于恍然大悟,五条人身上某种奇异的特质,究竟源自于哪里。
《热天午后》剧照
像仁科和阿茂这样深受电影影响的"非电影工作者",在当今的时代绝非少数。影迷之间自有暗语,当他们像呼吸空气一般流露出观影欲望时,当他们的谈论范围从在豆瓣TOP250延展到费里尼和塔可夫斯基时,当他们开始比较不同放映厅音响的细微差别时,他们已经成为了电影创作者和普通观众之外的第三类人。
相比把进电影院当做娱乐消遣的普通用户,影迷们的观影往往更加虔诚、拥有十足的仪式感。
“有次看电影时,一个女生的电话铃声在几分钟内连续响了两次,现场五六个影迷真的就暴跳如雷了。最后那位女生直接被赶出了影厅,再也没回来。”一位影迷回忆了他在电影节上,经历过的“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次观影经历”,而在很多影迷心里,这种“愤怒”是很容易被理解的:电影节的展映,或许是很多影迷一生中唯一一次,能在大银幕上看某部电影的机会。
这种痴迷,当然不仅仅属于年轻人的专利。“看了十几年电影节啦”、“每个周末都会去电影院的”……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环节的第一天,费里尼的名作《八部半》开场前,毒眸(微信ID:DomoreDumou)在上海影城门口遇到了一位上海阿姨,年过五旬的她,兴奋地和我们讲起了自己身处一个十几个人的影迷圈子里,每当遇到某部心仪的片子时,他们总相约观影、阵势浩荡。
而相比创作者,影迷们又拥有更纯粹的旁观者眼光。他们对影片质量有着自己的一套严格标准,并总会在豆瓣上留下只言片语或洋洋洒洒数千字,与其说是一份表达,更像是某种和自我对话。
对电影行业来说,影迷不仅仅是电影在宣发前期的一股重要力量,也是影响着创作。今年在北影节放映的《绿光》,是法国导演侯麦的代表作,而《绿光》的主演兼编剧、侯麦御用女演员玛丽‧里维埃和侯麦结识,靠的是她在21岁时写给侯麦的一封信——那时候,她还只是个普通的影迷。
《绿光》剧照
其实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上海就已经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影迷团”。“影迷团”团长、《影迷周报》赵英才专门强调了影迷如何影响着电影发展:“影迷是维持电影与创造电影的‘最后力量’,是纯真的影迷和广大的观众。他们不但是‘最后力量’,而且是‘最高力量’。”
影迷和电影这种特殊的联系,前后延续了百年之久。而在今年,这一切都变得更为特别:
由于疫情,大批影迷数个月的时间里无法进入影院。以至于当影院复工后,上影节、FIRST青年电影展、北影节三大电影节先后在7-8月间召开时,很多影迷开始进行报复性观影,电影节成为了平日里四散各地的他们的欢聚地。“泡在电影里真的很舒服,尤其今年大家都憋坏了。”刷完自己的北影节片单后,一位影迷心满意足地说。
这两个月里,毒眸也先后亲身参与了这三场狂欢,见证了中国影迷的众生相,这是关于他们的故事。
做电影的俘虏
7月的一个傍晚,上海影院旁的一家面馆,一个20多岁的年轻男生走了进来,匆匆地点了一碗黄鱼面,顾不得面条还有些烫,便大口吞咽了起来。
几分钟后,另一个刚刚从外地赶到上海的男生,坐到前者身边与之攀谈了起来,并从包里掏出了两张电影票。这是同在一个影迷群的他们,第一次见面。20分钟后将开始放映的一场《大地》,就这样将两个素未谋面的电影爱好者连接了起来。
每年的上影节,都是全国电影爱好者的大型“面基现场”,而在今年座位、场次都严格受限的情况下,团队作战更是成了一种常态。
有位女生为了给两位朋友求得两张《现代启示录》,在各大抢票群进行了数轮换票,终于在六轮的“交易”后,凑齐了三张一同欣赏科波拉的“入场券”。“今年抢到的每一张票都很珍贵,得像金币一样来交换。”这位影迷笑着向毒眸展示了她手中来之不易的电影票。
《现代启示录》海报
这是她第五次参加上影节的展映,她今年的目标是要看够20场,而在她的认知里,“骨灰级影迷”一次电影节下来往往能看三四十部影片——在没能如愿抢到票的情况下,另一位请了年假从北京赶来上海的资深影迷,每天一早就守在想看的电影放映影院门口外,还时刻盯着手机里的转票群,看看有没有人临时转票。在他的周围,还有不少人则举着手机、灯牌,“求《八部半》、求《红辣椒》”的字眼格外显眼。
而上海这片令影迷们癫狂的土地,正是中国影迷文化萌芽的地方。
1896年的上海徐园“又一村”茶楼里,西洋影戏第一次走入中国人的生活。在《火车进站》这样的影戏从幕布上隆隆驶来的12年后,电影从茶楼离开,有了专属的放映空间,那便是最初的影院。全中国第一家影院,坐落在上海的海宁路乍浦路口,是一座铁皮搭建的、可容纳250名观众的“铁房子”。
到了20世纪20年代,电影已经成了很多国人最重要的娱乐手段,《电影杂志》《影戏杂志》这样的刊物热衷于描绘观众对电影的迷恋:“每出一新片,虽身负要事,亦置诸不顾,必以争往先观为快,见片之至佳处,常喜极欲狂”、“一见国产影片出映,就像磁针见铁一般,必定要去看了”。
1925年的《影戏世界》杂志上,刊登了一封署名为“思廉”的读者来信,开头便是“我是个影迷”。这是“影迷”一词,第一次出现在公共舆论里,自那之后,这批热爱电影的人便有了统一的代号。鲁迅先生算得上是当时中国影迷的代表,1927到1936年的十年间,他在上海看了约140部电影。每每观影,都会在日记上写下“佳”、“不佳”或“劣极”的评论。
图源光明网
此后的数十年里,社会经历了战乱等动荡,电影创作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已有了雏形的影迷文化,却还是在历史长河中被传承了下来,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迎来了再次萌芽的机会——在一间间混合着烟草气和汗臭味的、30多平米的录像厅里,无数70、80后生人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了港片和好莱坞大片等“新鲜玩意儿”,在追视听刺激的同时,也有一部分人慢慢感受了影像语言的魅力。
《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迷影文化研究》一文提到,中国当代的迷影文化于90年代的盗版影碟中萌芽,发轫于电影酒吧的小型公开放映,成形于21世纪初的DVD观影和网络社区。而普通人的观影轨迹也大致如此,不同年纪的影迷,对电影最初的记忆并不相同。
对于很多90后影迷来说,VCD与DVD是他们关于电影最真切的记忆。
在90后影迷JoJo的回忆里,她是从50张DVD开始接触电影的:“5年级的暑假,爸爸买了一台DVD回家,还有碟店老板帮挑的50张DVD,其中的《黑衣人》陪伴了我整个青少年初期。”在整个初高中时代,JoJo成为了碟店常客,也慢慢开始懂得电影的更多可能性。
数据显示,2000年-2003年期间,国内VCD的数量从0.79亿张增长到3.05 亿张,而DVD的2002、2003年发行数量也比同比增长了614.4%和168.26%。
2005年,19岁的仁科和24岁的阿茂一起住在广州最大的城中村内石牌村,石牌村里有发廊,也有盗版影碟。卖盗版书和打口碟之余,他们通过同行接触了大量的盗版电影。关于“五条人”这个名字最为文艺的一个说法,是仁科和阿茂化用了杜可风的电影《三条人》。
这些盗版内容毫无疑问都是处在灰色地带的产品,但在信息交互不够发达的年代里,浸润了太多的观众甚至是创作者。
贾樟柯就曾回忆道:“在当代商城附近的一家商店,我同时买了两张 VCD 光盘。一张是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一张是奥威尔斯的《公民凯恩》…… 当车过大钟寺附近楼群里的那片田野时,突然意识到我用几十块钱,就把两个大师的两部杰作装在了自己的口袋里,心里猛然的一阵温暖。”
正如《新青年DVD手册》一书的卷首语中所言:“我们并不介意将那些引进了伯格曼、帕索里尼给普通大众的暗黑(盗版碟)商人与盗火的普罗米修斯相提并论。”
但也正是因为有过这样一段游走在边界上的岁月,而今的影迷对电影的“敬畏感”反倒更为突出。
在北影节抢票正式开始前,很多影迷都会加入十几个、甚至几十个500人的大群,抢票开始前的几分钟群里人声鼎沸,抢票开始的一瞬间群里顿时鸦雀无声。
短短几分钟后,群内再次开始沸腾,大家纷纷把群昵称改成自己的求票、换票信息。管理员则会不断提醒,严禁加价转票,这似乎成为了很多人默认的一种规矩,对电影的爱是不应该被利益所裹挟的。
图源:某微信抢票转票群
而在今年FIRST期间,西宁白日的地面温度直逼40度,可即使是不算大热门的纪录片《光之子》,仍有人提前一个小时在放映所在地青海大剧院门前开始排队。大剧院门口毫无遮蔽,在高原强烈的日照下暴晒过的观众们,进门测温时的体温纷纷突破40度、没法通过安检。大家只好在一旁扇风,等待体温降下来。
电影开始后,这种敬畏感更被放大了。
2015年6月,上海影城二厅即将放映金爵奖竞赛片《岸边之旅》,一位观众突然走上舞台,向在场的所有观众说出了一段话:“大家好!我是一名普通影迷。为了保证大家观影愉快,请每位朋友在暗灯后放映中不要拍照,不要摄像,手机请挑静音,调低亮度,减少使用频率。请勿大声喧哗,尽量不说话。总之,尽我所能,不打扰他人。也请工作人员加强场内巡视和监管。谢谢大家!”
一位亲身经历、见证过上述这几件事情的影迷告诉毒眸,跑了很多年电影节的她,常常会感到孤独,身边的一些人会觉得自己“太文艺”,无法明白为什么要花很多钱跑去上海看网上资源随手可及的老片子,更不懂她为什么要跑到西宁这么远的地方去看一些不成熟的新人作品。
可当她真的经历了这些事情、见到了这些人的时候,却慢慢意识到和自己类似的人其实有很多,自我对电影痴迷的心境有了回响。“人有时候可能真的很需要找到一个让自己很狂热的事物。参加电影节,加入到一个集体性的行为中去,可能会有找到支点的感觉,不会那么孤独了。”
和数位影迷的交流中,毒眸发现,不少人的教育背景和如今的工作和电影毫不相干,但是电影却像他们的恋人、也像他们的朋友,是他们生活的底色。“只要空下来,就会看电影。”
或许就像杨德昌在《一一》里说的:“电影发明以后,人类的生命比以前延长了三倍。”
本质上,这种痴迷的心理是因为电影这台强大的造梦机器,很容易让人们在观影的快感中,拥有陶醉的认同感。《重点所在》一书提到:“电影具有典型的现代性,为人们喜闻乐见,诗情与神秘感、色情与道德存于一体。”在电影的幻梦中,人类的个体孤独被消解了。
影迷如何改变电影?
影迷不仅仅在和电影对话,也以一种隐秘的方式,改变着电影行业。
在电影进入中国十数年间,国产电影欧化的现象依然非常严重,西装、洋房、舞会等元素一度充斥着国片银幕。慢慢的,包括影迷在内的一些精英知识分子开始希望改变这样的风气,于是便开始挖掘民间文学,提出渴望在大银幕上看到真正带有中国文化属性的影片。
在经过“梁祝化蝶”这样的故事改编成《梁祝痛史》的试水后,1928年,同为民间故事改编的武侠电影《火烧红莲寺》在上映后取得了巨大成功,三年连拍了18部续集。《火烧红莲寺》能流行开来,很多程度上是因为在积贫积弱的国情下,影迷和普通观众都在片中寻找到英雄主义情结的寄托。
在那之后,更多的片厂看到了机会、受到了启发,在创作上从全面欧化掉头,开启了三年的武侠神怪片潮流——1928年到1931年的400部国产影片里,250部是类似《火烧红莲寺》的故事。《火烧红莲寺》偶然为之的尝试,却也是民间的影迷意志第一次打破官方主导的里程碑,电影的制作方向开始被影迷影响。
《火烧红莲寺》海报
到了今天,影迷则成了一部分电影能够继续生长的土壤。美国的ABRAMORAMA公司早年专注于发行各类乐队纪录片,而他们能为很多小众影片博取数百万美元的票房,靠的便是精准找寻受众,只在最有把握的地方(best locations)发行。在发行之前,他们会确认这部电影是否具有tribal(部落)属性,也就是是否已经存在核心观众。而他们的工作,就是识别和动员他们。
即使后来开拓了国际发行渠道,ABRAMORAMA依然遵循这样精细的打法。2019年下半年,为了发行蓝调摇滚乐队ZZ Top的电影,公司在两个半月的时间内,一路跟随乐队的50周年巡演,每到一个巡演地点,就在演出地所在的城市放映4-7天相关影片。
在当下的全球电影产业里,影迷文化不止对ABRAMORAMA这样的独立发行商很重要,同时更是整个电影工业里的关键一环——大众流行文化的审美裹挟和好莱坞大片的全球发行模式,导致主流渠道的内容开始趋同,而影迷“特立独行”的选择,便显得尤为珍贵。
上海大学教授葛颖指出,电影正从一种文化消费品转变为快消品,消费者的购买习惯是:简单、迅速、冲动、感性。大环境的变化带来了审美多样性的匮乏,这点从2016年北影节上的一个小插曲可以窥见——
当年塔可夫斯基的《镜子》,被许多观众大呼“看不懂”,北大教授戴锦华对此颇为不解。她表示,当《镜子》于1975年公映时,曾让整个莫斯科为之沸腾,而北影节部分观众看不懂的背后,是“很多人对单一审美趣味的洋洋自得“。戴锦华甚至尖锐地指出,电影教育是作为人文教育的一部分,作为一般的艺术教养和艺术修养,在中国还远远不够、甚至很差。
《镜子》海报
这种生态,对一部分影片生产空间的压缩是可想而知的。去年在戛纳上大热的《春江水暖》,便在发行过程中遭遇了不少阻力,其制片人黄旭峰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市场上能够聊一聊的、最好的、有可能发的发行公司我几乎都跑过”,但出于商业考虑,这些公司的发行意愿普遍不高。
事实上,早年间国内的艺术电影常常寄希望于先在国际上得奖,再回国上映。而如今即便在影迷文化最好的欧美地区,迷影运动也早已式微,影迷多为中老年人,年轻人多数对艺术片不感兴趣。2019年戛纳电影节期间,就有很多跑了很多年电影节市场的从业者告诉毒眸:“除了好莱坞商业大片,多数国家的电影现在想出海都不容易。”
故上海师范大学硕士生王梦昭在《艺术院线在中国的困境与出路》一文中提到:“艺术院线要发展下去,至少要具备三个前提:第一个是稳定的观众群,第二个是充足的片源,第三个是资金支持。”
而其实不仅仅是艺术电影,很多现实题材、纪录片,甚至是《信条》这样具有一定观影门槛的影片,在宣发上都会在不同程度的依赖影迷群体,希望通过他们来发酵口碑。
全部启用藏族素人演员、和《变形金刚5》同期上映的《冈仁波齐》最终收获一亿票房,依靠的便是专攻一线、新一线城市的核心影迷。这样的精准营销保证了口碑的持续发酵,使该片能在数周的时间内、始终保持单日百万量级的票房成绩,完成长线积累。拿下《小偷家族》国内版权的路画影视CEO蔡公明也认为:“文艺片是口碑电影,依靠忠实粉丝的口碑传播,把核心受众维护好,就已经完成大部分宣发工作了。”
很多商业片成功的背后,同样有类似的故事。
2015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上映初期,受观众认知度影响,影片热度不是很理想。于是大批看过影片的影迷,便自发组织包场、送票等各种活动, 还开设了“水帘洞大圣自来水公司”的自来水微博, 每天更新票房动向等。
一位影迷在回忆自己充当《大圣归来》的“自来水”的经历时说,“我感觉自己参与了电影的宣发过程,看着《大圣归来》的票房一天天好起来,排片也越来越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自豪感。”
《大圣归来》海报
到了今天,类似的模式已经在很多影片上被复制,甚至开发出了很多新玩法。《我不是药神》在上影节期间的“千人点映”,主打媒体和资深影迷,成了这部现实题材作品,在日后口碑不断向下辐射,最终能在竞争颇为激烈的暑期档,面对很多商业大片一骑绝尘的关键。
除了对宣发、影片内容方向的影响,在影迷群体中,还孵化出了影评人这样值得单独被讨论、深刻影响着产业的群体。
1954年,24岁的《电影手册》编辑、影评人特吕弗采访了电影大师希区柯克,在这次采访中,特吕弗终于见到了偶像,体会到了“作为影痴的无上幸福”。虽然彼时的特吕弗只是个毛头小子,但还是以此为机缘,和希区柯克建立了终生的友谊,在和希区柯克的交流中不断从这位前辈身上汲取养分。和希区柯克初次见面的5年后,特吕弗拍出了《四百击》,为法国新浪潮运动拉开了序幕。
《四百击》剧照
这种“反向的影响”,在当下的时代环境里正变得越发普遍。在互联网并未普及的时代,迷影者们各自看着碟片,互相并不知晓,专业话语权还掌握在学者、官员、专业杂志上。而当网络的接口打通,Liar、愤怒的猪猪、张小北等一批影评人相继涌现,网络让电影评论拥有了大众向的声音,进而成就了一类特殊的KOL,让他们有了向电影产业更上游迈进的机会。
在内容领域,电影圈活跃着不少影评人的身影。
前文提到的Liar,线下的身份是拍出了电影《少女哪吒》的李霄峰,在今年的上影节上,他的新作《风平浪静》入围了本届金爵奖;愤怒的猪猪,是拍出了《可可西里》《南京!南京!》的陆川;至于因为《第十放映室》而被更多人所知晓的张小北,也成为了一名编剧、导演,创作了《拓星者》等影片。
在促进宣发等产业端中下游事业发展上,更是有不少影评人在身体力行。
影评人卡夫卡•陆所所创办的“影像现场”是一项民间放映活动,曾名噪一时。虽然卡夫卡•陆在创办次年的2007年就不幸车祸离世,但其他影评人接棒管理,如今该组织依然活跃,致力于小规模的公益放映。在艺联出现之前,由影评人水怪等人创立的“后窗放映”项目和宣发公司放大影业,曾经填补了艺术电影在和普通人见面渠道上的不足。
此外,时年25岁的海关公务员“妖灵妖”徐鸢,早在1997年就开始带领着他的电影101工作室帮忙上影节组委会招募志愿者,电影101工作室成为了上影节筹备工作中一股重要的民间力量。今年上影节、北影节上《祝福》能以4K形式和观众见面,就离不开徐鸢在背后做出的工作。
《祝福》海报
不过有幸能够做电影、改变电影的,是少数影迷。更多情况下,电影进入了这些人的生活,成为了他们生活肌理的一部分,构建起了他们的部分人生。影迷的最终定义,或许就在一场场“集体地独自观影”中,反复在光影中相遇的痴爱者。
关于这种痴迷,一位有三万知乎粉丝的影迷和毒眸分享的一个故事:在大学时,有一阵他精神压力极大,而翘课去看《阿甘正传》的经历治愈、滋养了他。当看到阿甘对病床上的珍妮讲述自己在越南丛林看到的星夜和在落基山脉看到的晚霞时,他意识到,人人都有享受电影、享受精神生活的权利。
或许就像《看一场周末电影》唱到的:
看一场周末电影
让自己与故事中的人物暂时联系
看一场周末电影
让自己暂时活在荧幕上的故事里
看一场周末电影
让自己暂时发挥精湛的演技
参考资料:
1.和五条人一起找猪,GQ报道
2.仪式性展演:上海国际电影节影迷参与实践的研究,黄经纬,南京大学
3.民国时期影迷研究,喻筱程,贵州师范大学
4.中国早期电影观众史(1896-1949),陈一愚,中国艺术研究院
5.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迷影文化研究,李佳瑛,中国艺术研究院
6.让电影、影迷和电影节一起成长,从易,解放日报
7.电影口碑传播中“自来水”的形成因素研究,赵蓓,现代视听
8.从《大圣归来》看“自来水”式的电影宣传策略,宋超,经贸实践
9.当我们只知影迷而不知迷影,葛颖,解放日报
10.特吕弗:影迷的梦想,连城,电影世界
11.奖项在手也难逃院线放映取消,文艺片发行仍然困难重重,第一财经
12.电影十日谈6.18. 忍无可忍的观众走上了舞台,电影山海经
13. Deadline| Abramorama Seals Film Fund Deal To Turn Up The Music| Patrick Hipes
14.ScreenDaily| Abramorama expands into international distribution (exclusive)| Jeremy K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