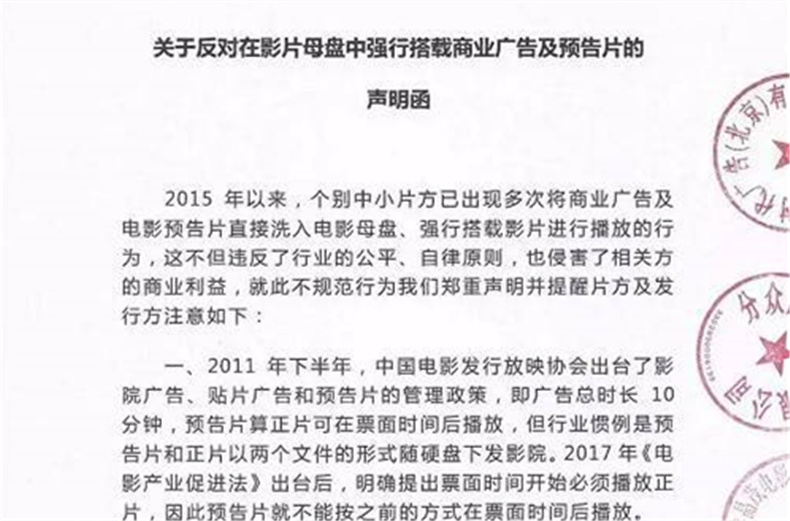惊奇电影创投会
作为主打科幻、奇幻类型电影的电影节,惊奇映像节的主题是“极客×想象”,通过展映、创投、论坛、电影嘉年华四大主体活动,向市场和观众推出具有前瞻性的科幻、奇幻电影项目,探讨中国科幻、奇幻类电影以及相关文化的未来。而其中最具特点的是惊奇映像节在国内首度推出跨界导师和评审机制,为入围电影项目和导演提供创作、科学顾问、概念设计、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将项目展示和先导概念片结合,让科幻、奇幻IP实现有效转化。

王红卫
为此,惊奇邀请有丰富制片经验的导师进行指导,王红卫成为惊奇·幻想实验室支持下的第一届惊奇创投活动的首席导师。作为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副会长,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教授与硕士研究生导师,他参与编剧的《疯狂的石头》一举斩获金马奖最佳原著剧本奖,与宁浩导演携手创作的《疯狂的赛车》、《黄金大劫案》、《无人区》等,都无一例外地成为票房收割机。而王红卫本人对于科幻题材也有很大的兴趣。在他看来,未来的中国电影市场中科幻将成为一大趋势和热点。这也是他加入惊奇映像节的主要原因。
Q:科幻在国内电影圈这两年比较热,您怎么看待这种科幻热?
王红卫:雷声大雨点小,是趋势也是热点,趋势就是行业发展到这个地步,从更大的环境和更长的坐标轴来看应该发展。但热点就不同了,作为热点,里面就必然有某种凑热闹炒概念的短视和图利的成分。
这里面有些现象,其实是和宁浩做完疯狂的石头之后,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时候我俩在他家楼下一个饭馆喝酒,说起来下一步的打算,大的方向我当时觉得应该做科幻,当时是2006年的夏天,现在看来确实还是想得太早,后面也没有马上启拍科幻。但是又过了几年,宁浩的夫人把刘慈欣的《乡村教师》推荐给他,才有了现在《疯狂的外星人》的雏形,但意识上的准备其实很早就开始了,这是一个小故事。
而我接触的电影界的导演和作者啊,实际上有一个代际的问题,从四代、五代到六代,从我的老师到我这一辈,我碰到的人里面很少有人对科幻感兴趣,这和每一代人的成长经历会有关,尤其和童年、少年所接触的东西有关。尤其在中国60年代出生的人,他们所接触的科幻还是非常非常少,到我这里60末、到改革开放才有接触。所以我觉得如果说科幻成为某一个时代的文化、娱乐热点,还是基于这一时代人的童年文化涉猎范围。如果说他幼年没有接触,青年时代就不会有追求这个题材的需求,中年也不会有相应题材的创作欲望。而中国现在实际上是80后和85后的编剧和导演开始成为这个舞台的主力,他们青少年的时代,《科幻世界》这样的杂志已经是他们经常接触的读物了,国外的科幻电影已经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国内了。所以在他们这一代,这种趋势和土壤已经形成了,我觉得他们再做科幻,就不是一种跟风或简单的行业趋势判断,而是一种内在由衷的创作冲动,所以这实际上是一种创作者的队伍准备。如果说每个时代拍摄的作品主要是给同时代包括同时代之后的人看的,那么观众的土壤也同样趋于成熟,已经有了一定的群体。

《捉妖记》
从行业而言,我们也出现了题材的短缺。对比好莱坞,我们没有那么丰富的电影类型,因为观众的接受程度和电影环境、电影政策的原因,有些内容我们不能拍,所以我们能够打开市场的类型很少,大家都去拼那几个固定的类型,自然会造成现在的状况,比如说我们平民喜剧拍了一部又一部,慢慢就会转向《捉妖记》这样的题材。题材类型短缺的情况下,科幻是一块肥肉,行业资本的趋利性会向科幻这个方向靠近,这是行业天然的动力。
第三就是,随着现代的科学技术和我们制作能力的提高,可能这里面有另外一个驱动力,比如说如果我们要把产业做大,那么我们需要有特效公司,特效公司的工作如果还是只停留在现实题材的绿幕、动作和飞车还是比较老套的,所以我们建立和购买特效公司之后,也会有进一步制作科幻电影的需求。同时现代的科技产品消费也会产生一些比如科技爱好者、装备控这样的消费者,他们的爱好也会影响观影需求。这样的话各方的合力让我们觉得中国电影在制作和市场层面已经打开了一扇门。到2015、2016年,已经有不止一部科幻电影在开发制作当中,大家都等着科幻片的热潮,是一种必然趋势。但我们还是要冷静一些,希望在刚开始的阶段,可以带来更多成功些的作品,不要往刚燃起来的火上泼太多的水。

惊奇映像节
Q:您对科幻电影一直有关注吗?最近是否有参与到一些科幻项目之中?
王红卫:有一直关注,但很长一段时间是作为一个观众,一个爱好者,和自己的教学和创作没啥大关系。最近几年参与了一些科幻项目,最近在做的就有两三部个电影和一两个剧。
Q:惊奇映像节主打的是科幻和奇幻,您参与这个电影节的初衷是什么?
王红卫:个人兴趣,科幻奇幻魔幻,还有cult和恐怖等等,这算恶趣味吧,还有就是就是刚才说的,我觉得趋势还是必然的。
Q:幻想实验室三个先导预告项目的新人导演的创作中,是否代表了年轻一代电影创作者在科幻方面的特点和问题?您怎么看待这些问题?

国外科幻电影成为主要营养
王红卫:第一就是科幻意识还是不够强,没到科幻迷的程度。他们三个从和我讨论脚本开始,营养来源还是来源于以往看过的科幻电影以及衍生出来的周边知识,还没能离开这个特定的营养母本。比如说,如果你本身是电影背景出身,但从原来就接触科幻和科技知识,那么知识储备和创作来源就会不一样。虽然我们是在寻找有电影基础的创作者,但我更希望以后的创作队伍可以有资深科幻迷,或者有些人可能是学习屋里、计算机等等其他学科,有时他们会有一些看起来有些幼稚、离电影很远的东西,但是那些东西反而是会激发更多创作灵感。
如果一个创作者只是有一个电影背景,但看到现在大家都在做科幻,临时找来一些书籍和电影看看,就觉得明白了科幻开始进入这个领域,这个是有先天不足的。这方面我们和国外不同,国外有些导演确实没有过硬的科幻基础,但他周围的人才梯队和土壤非常健全,他能够找到相应的支持。但中国的状况,一直做电影的人知道,只能靠自己,编剧、摄影等等其他角色往往也并非某个内容领域的专业人才,没办法成为这方面的有力助手,在中国导演创作还是靠自己的知识储备,不能指望有「外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幻类型和其他类型就不会一样,需要的很多知识是电影之外的,这对于外来的青年科幻电影人来说很重要。
第二就是全行业可能还都存在的问题,电影的理念和手段技巧层面,都相对还缺乏。为什么这个问题我在科幻电影问题上还是要强调一遍呢,因为科幻电影对这方面的能力要求要超过一般的文艺、喜剧、警匪这些类型电影,首先从编剧的基础和知识要求更加缜密,知识背景要更丰富。电影叙事的视听表达方面,也要更精确,要更善于用视觉化的东西,把抽象概念呈现给受众看。而且科幻电影往往需要用这100分钟的空间,来实现完全处于我们日常生活经验之外的世界观设定,甚至会在这个基础上设计非常紧张、惊险的故事架构,或者为了让观众有更多情感共鸣,而进行亲情、爱情的表达,所以科幻对导演的要求就骤然提升,它会比一般的电影要求导演在电影基本功的层面更完整更精准。现在市场上有一些非导演出身的人刚拍作品就还不错,我觉得不是别的原因,可能是因为难度还是比较低,换做科幻,难度就非常高了。
第三就是想象力的问题。因为我一直做老师,从80后开始到现在,好像越来越不能让人满意了,越来越缺少天马行空的东西。其实创作类的艺术院校,都希望一代一代学生中可以越来越出现我们所不能简单理解的创意,和超出我们经验范围的东西,这个我们不仅不会反感和抵触,其实我们会高兴,而且当不止一个在做的时候,他们之间可以沟通,我们只能在一旁听着发呆,我觉得这是好的,是对的,但却一直没有出现。原因可能与基础教育有关,与整个给社会的大环境有关。如果说你做一个常规的影片,那没问题,但如果要做科幻,那就会有问题,创造力的缺失产生的不止是不足,有可能会变成致命的缺陷。同时对于中国的科幻而言,如果想要后发制人,打开更加宽阔的外部市场,单纯的模仿肯定是不够的。
Q:在我们当下中国科幻电影的起步阶段,可能您刚才提到的问题不会是个例,您认为在编剧创作层面,科幻电影剧本改编需要注意什么?
王红卫:第一:还是中国化,中国观众认可最重要。
第二:对于科幻迷出身的编剧导演而言,要强调故事比科幻点重要,而对于擅长非科幻类电影的编剧导演而言就是反过来,科幻点和知识很重要,理解科幻片很重要。
电影是个名利场,有很多人拍电影是为了当导演的虚荣,这样走不远,同样的道理,大概十几年前开始的商业电影时代,我就频频遇到本来爱好文艺片的导演一定要拍商业片,完全不看恐怖片的导演要拍恐怖片,所以可能如果你不喜欢科幻,因为它可能会是个热潮就来拍,会很事倍功半。
第三:最好的科幻电影光有科学知识不够,光有电影技巧也不够,其实需要对宗教、社会、文化,人类本身的一些本质性的问题,都有思考才能做得好,这个在中国的电影人中很难。
Q:您为什么会觉得第三点在中国电影行业内还是比较缺失的?

《火星救援》中涉及大量科学知识
王红卫:首先要声明一下,我所说的科学知识、电影技巧和深厚的人文知识意识是制作顶级的科幻电影所需要具备的,如果说是起步阶段,我觉得还是不要过早的把自己的入手点直接局限于太高的层面。
如果我们来讲一些经典的科幻作品,我觉得宗教、社会、文化,对人类这些大的议题是必要的。但为什么说对于我们来说是特别难的呢,因为我们算是活得特别现实的一个民族,我们一般不太会去想那些和我们现实无关的东西,或许文化基因如此,这是一个大的问题。具体到电影人就更不容易,从电影工业发展,到受众水准到一些环境政策的影响,一直是在一些很有限的条件之下做电影,所以理想层面上的东西可能会被阉割的比较多。大家能拍一些有人喜欢看又能自我表达的东西已经不易,至于说拍一部「我这辈子最想拍的电影」,那对于很多电影人来说还是望尘莫及的。另外宗教发展在中国还是比较薄弱,科学发展也有限,哲学方面,还是以一种意识形态为先的方式进行教育,因而这些导向终极问题的领域发展先天土壤不充分,那么导致一个创作者去思考这些问题的可能性就很小。现在做科幻,设定方面如果落在大家都比较能够理解的范围之内,那么可能会做出比较有亲和力的科幻作品,但离伟大的科幻作品,相对而言还会有距离,这方面目前可能不太乐观。

惊奇·幻想实验室
Q:当下科幻类型普遍是以欧美的作品为主导,并且他们已经建立起了相应的核心概念和美学体系,我们中国人现在想要拍摄科幻片的话,涉及到要不要参照西方科幻的思路,从文化和审美上都会面临不少尴尬的局面,在「学习借鉴」与「本土化」平衡的过程中,您觉得如何在创作阶段找到更好的切入点?
王红卫:这是我们起步时最重要的问题,要是我知道一个能简单说清楚的答案就是穿越过来的了,大家都在摸索,但是一定有我们的方法,而且不止一种,看谁先找到,要说如何找到切入点,那就是先搞明白当下的中国人,再去找这个点就会准确度提高,要是你连中国和中国人是咋回事都还稀里糊涂,那就容易做出山寨感和雷人感很明显的东西。
Q:在文化理念、概念设计这些方面,中国还是有着自己的独特传承,电影工业发展、市场受众上也有自己相应的特点,您认为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科幻片拍摄上的优势和劣势分别在哪?
王红卫:优势是环境,行业好,资金流,大量科幻到中国来寻求投资。
劣势是创作队伍和创作经验,包括制作经验,这几年中国电影更喜欢的是小投资爆款,说白了就是投资效益最大化,这种追求的坏处就是制作感低,市场份额占比,绝对单片票房都有数倍增长,但现代电影制作技术的差距没有因为缩小。
Q:中国科幻电影现在还处于起步阶段,我们都明白整体的行业发展也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当前的三个项目算是我们试水科幻电影的一个尝试,您觉得以这三个项目呈现出的特点,在中国电影市场中各自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潜力?
王红卫:这三个项目都是主办方和以科幻见长的评审们千挑万选出来的,我觉得共同的特点就是在目前的环境下,都有可操作性,而故事种类也基本覆盖了主流硬科和偏硬的科幻的类型,都可以作为科幻电影起步的试验田。
从一开始和惊奇团队接触,觉得他们对科幻有热情,这种状态就是最好的。具体到这三个项目,《拯救人类》是一个废土片,《时空乱流》是一个太空硬科幻,包括其中产生的平行宇宙,《七重外壳》是有关意识、身体、梦境这些基础概念,我一直觉得《七重外壳》可以发展的是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它可以向软科幻发展,所以这几个方向可能是既有的几个科幻类型里的几个大方向,首先就是方向岔开了,其次就是这几个方向都还是非常有操作性的,我们学习借鉴的标本会比较多,所以我觉的这三个项目是非常可行的。
但这三个项目长远来看,在市场上,光有这三个先导概念片是不够的,还是需要落实到后续公司接手上面,需要更有实力的团队来帮助这几位导演,或者找到其他的导演来完成。但是我又保持一定程度乐观,因为从之前的讨论来看,以这三个项目的基础,还是能够以现在我们的资金条件和制作条件去完成,所以但愿它们能赶得上科幻电影的这波热潮,成为第一批或者第二批能够真的制作完成的片子,算是我一个良好的愿望。
同时要注意的问题就是,这三个片子都还处于概念阶段,往下走要遇到的第一个问题都是剧本,因为这类片子怎样来操作,都是没有先例的。剧本之后才是创作和制作团队的其他问题,那么这次创投之后,在你们去寻找未来的合作伙伴的问题上,我觉得能否把握准这三个项目的发展方向非常重要,包括对方到底是否懂科幻,并且知道它们的边界在哪——既不能太大,在刚刚试水的中国科幻电影市场上,又能够找到和观众的以往观影经验相结合的点。对于这个问题,决策层的方向非常重要,你们是一个孵化器,就像是一个「代孕妈妈」,那么之后「胚胎」如何转移,谁是新的「父母」一定要慎重选择,其实难度很大。
Q:您对中国做科幻电影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王红卫:大胆假设,小心求证。